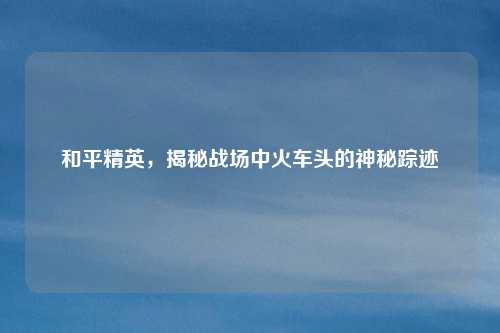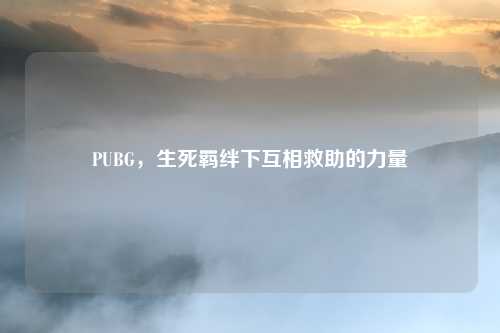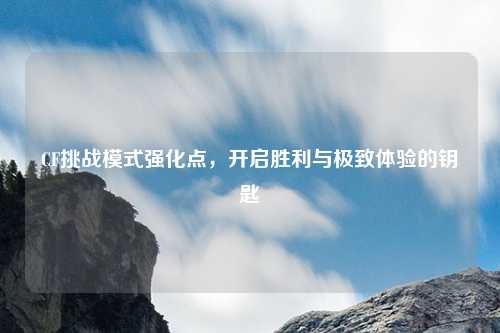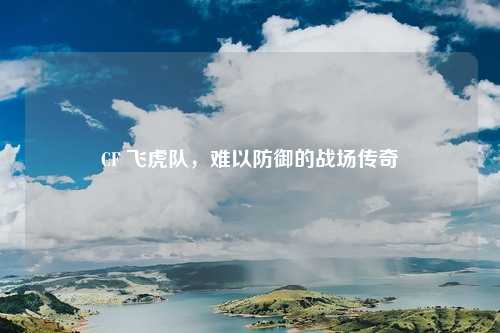在乡村的记忆长河中,赶驴是一幅独特且生动的画面,那一头头身形矫健或略显憨态的驴子,拉着车、驮着物,在乡间小道上踏出深深浅浅的印记,而赶驴人则跟在一旁,吆喝声与驴蹄声交织,奏响一曲别样的生活乐章。
小时候,村子里的王大爷就是个赶驴的好手,他那驴车,是村里孩子们眼中移动的“乐园”,王大爷的驴子叫“黑宝”,浑身黑得发亮,唯有额头正中有一块白色的毛,像是镶嵌上去的宝石,每天清晨,阳光刚刚洒在村子的屋顶,王大爷就会走进驴棚,一边轻声唤着“黑宝,黑宝”,一边给它添上新鲜的草料和清水,黑宝总会亲昵地用脑袋蹭蹭王大爷的肩膀,发出“嘶嘶”的叫声,仿佛在回应主人的关怀。

准备出门时,王大爷熟练地给黑宝套上鞍辔,牵出驴棚,黑宝似乎也知道要开始一天的劳作了,迈着轻快的步伐,跟在王大爷身后,驴车是一辆简单却结实的木板车,车轮是木质的,边缘镶着铁条,虽比不上如今的橡胶轮胎,但在乡村的道路上也能稳稳前行,车辕上挂着一串铃铛,随着黑宝的走动,铃铛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,在寂静的村子里传得很远。
王大爷赶驴去的最多的地方,便是集市,集市在距离村子十几里远的小镇上,每周有固定的日子开市,天还未亮透,王大爷就带着黑宝出发了,一路上,黑宝不紧不慢地走着,王大爷则跟在车旁,偶尔拍拍黑宝的屁股,嘴里念叨着:“黑宝啊,咱今儿个可得早点到集市,把货卖个好价钱。”乡间的小道两旁,是大片大片的田野,春天,油菜花金黄灿烂,微风拂过,花浪翻滚,黑宝偶尔会被这美景吸引,停下脚步多看几眼,王大爷便会笑着催促:“黑宝,别走神儿啦,赶路要紧。”夏天,绿油油的稻田像一块巨大的绿毯,青蛙在稻田里欢快地叫着,仿佛在为黑宝和王大爷的旅途伴奏。
到了集市,王大爷找好摊位,把驴车停稳,就开始忙碌起来,他车上装的大多是自家地里种的蔬菜,新鲜又水灵,王大爷一边叫卖,一边留意着黑宝,黑宝也很乖,静静地站在车旁,偶尔低下头啃几口地上的青草,集市上热闹非凡,人来人往,各种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,黑宝似乎对这热闹的场景也充满了好奇,眼睛滴溜溜地转着,看着周围的一切。
赶驴的日子里,也不乏有趣的小插曲,有一次,黑宝在路上看到一只野兔,一下子来了兴致,撒开蹄子就追了上去,王大爷在后面又急又气,一边大声喊着:“黑宝,回来!回来!”一边拼命追赶,黑宝哪肯罢休,跑得那叫一个快,把王大爷远远地甩在了后面,等黑宝终于追累了,停下脚步时,才发现自己已经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,王大爷好不容易追上来,累得气喘吁吁,看着黑宝那一脸无辜的样子,真是又好气又好笑,扬起手中的鞭子,却又轻轻落下,只是吓唬吓唬它:“你这调皮的家伙,下次可不许这样啦!”黑宝似乎听懂了王大爷的话,耷拉着脑袋,乖乖地跟着王大爷回到了驴车旁。
在农忙时节,赶驴又有了新的使命,黑宝会被套上石碾,在打谷场上一圈又一圈地转着,帮助村民们碾稻谷,王大爷站在一旁,手中握着缰绳,嘴里喊着号子:“嘿哟,黑宝,加油干呐!”黑宝听着号子声,脚步更加有力,石碾滚动的声音,和着稻谷脱壳的沙沙声,在打谷场上回荡,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耍,时不时跑过去摸摸黑宝的耳朵,黑宝也不生气,依旧专注地拉着石碾。
除了拉车、碾谷,黑宝还会帮着王大爷驮运东西,村子里盖房子,需要运送石料和木材,黑宝就成了得力的运输员,它背上驮着沉重的货物,脚步依然稳健,山路崎岖难行,但黑宝从不抱怨,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,王大爷跟在后面,心疼地说:“黑宝啊,辛苦你啦,等忙完这阵,给你多吃点好吃的。”黑宝似乎感受到了王大爷的关心,时不时回过头来看看他,仿佛在说:“主人,我能行!”
随着时间的推移,村里的年轻人都陆续进城打工了,村子里的道路也渐渐铺上了水泥路,汽车、三轮车等现代交通工具越来越多,王大爷年纪也大了,赶驴的次数越来越少,黑宝也老了,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,王大爷把黑宝养在院子里,每天依旧精心地照顾它。
有一天,我回到村子,又看到了王大爷和黑宝,王大爷坐在门口的椅子上,黑宝静静地站在一旁,阳光洒在他们身上,仿佛一幅静止的画,我走过去和王大爷聊天,他抚摸着黑宝的脑袋,感慨地说:“这一辈子啊,多亏了黑宝陪着我,那些赶驴的日子,虽然辛苦,但心里踏实,现在时代变了,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,可我还是忘不了和黑宝一起走过的那些路。”
黑宝似乎也听懂了王大爷的话,轻轻地蹭着王大爷的腿,看着他们,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,赶驴,这看似简单的劳作,却承载了乡村岁月里太多的质朴与坚韧,那些赶驴的日子,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,是人与动物之间深厚情感的见证,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,镶嵌在乡村记忆的天空中,熠熠生辉,永不褪色。
在遥远的山村里,赶驴曾经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老李家的驴子,那是一头浑身棕毛的大家伙,名叫“大壮”,大壮体型壮实,力气也大得很,老李一家靠着大壮,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,维持着简单而又充实的生活。
每年秋收时节,大壮就成了家里的大功臣,田地里,金黄的麦子沉甸甸地低着头,等待着人们去收割,老李和家人挥舞着镰刀,将麦子割倒,捆成一捆一捆的,而大壮,则被牵到田边,背上驮着两大捆麦子,迈着沉稳的步伐,一趟又一趟地将麦子运回家,它的蹄子踩在松软的土地上,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。
回到家后,麦子被卸下来,堆在院子里,大壮也不闲着,它又被套上碌碡,在麦子上一圈一圈地滚动,将麦粒从麦秆上分离出来,老李站在一旁,手中拿着一根细细的鞭子,不是为了抽打大壮,而是在必要的时候轻轻一挥,给大壮指引方向。“吁——”“驾——”老李的吆喝声在院子里回荡,大壮听着这熟悉的声音,有条不紊地工作着。
农闲的时候,老李会赶着大壮去山里砍柴,山路蜿蜒崎岖,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,大壮小心翼翼地走着,背上驮着绳索和砍刀,到了山里,老李选好一棵粗壮的树木,挥起砍刀,一下一下地砍着,大壮就在一旁安静地吃草,时不时抬起头看看老李,当树木被砍倒后,老李将树枝砍去,把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,用绳索捆好,再搬到大壮的背上,大壮虽然负重增加了,但依然稳稳地走着,将柴禾运回家。
在村子里,赶驴也是一种社交方式,每当几个赶驴人在路上相遇,他们就会停下来,互相交流,谈论的话题无非是家里的农活、驴子的状况,有人会说:“我家那驴子最近胃口不太好,不知道咋回事。”另一个人就会热心地回应:“是不是吃坏肚子啦?喂点盐水试试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笑声在乡间小道上回荡。
赶驴的日子里,也有让人头疼的时候,有一回,大壮不知为何突然发起了脾气,怎么都不肯往前走,老李又是哄又是劝,可大壮就是站在原地不动,还不停地打着响鼻,老李没办法,只好四处寻找原因,最后发现,原来是大壮的蹄子扎进了一根刺,老李赶紧找来工具,小心翼翼地把刺拔出来,又给大壮的蹄子做了简单的处理,经过这一番折腾,大壮似乎也平静了下来,乖乖地继续赶路。
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,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,收割机、拖拉机等大型机械设备逐渐取代了驴子在农田里的劳作,老李看着这些新机器,既感到新奇,又有些失落,他知道,大壮的使命可能快要结束了。
大壮并没有被老李卖掉或者抛弃,老李把大壮养在院子里,每天依旧精心地照顾它,大壮也习惯了这种悠闲的生活,每天晒晒太阳,吃吃青草,偶尔,老李会牵着大壮在村子里走走,回忆那些一起赶驴的日子。
在另一个村子里,有个叫阿强的年轻人,他也赶过驴,阿强的驴子是他爷爷留给他的,那是一头小个子的灰驴,叫“小灰”,小灰虽然个头不大,但十分机灵。
阿强赶驴,更多的是为了生计,他会用驴车拉着自家种的水果去镇上卖,每天天不亮,阿强就会把水果装上驴车,然后赶着小灰出发,一路上,小灰总是走得很快,似乎知道要去做什么,到了镇上的集市,阿强找好摊位,开始叫卖:“新鲜的水果,便宜卖啦!”小灰则在一旁安静地等待着。
有一次,一个小女孩路过阿强的摊位,看到小灰,特别喜欢,就缠着妈妈要买,妈妈笑着问阿强:“这驴子卖不卖呀?”阿强连忙摇头说:“不卖不卖,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,是我的好伙伴。”小女孩有些失望,但还是不停地抚摸着小灰的脑袋。
赶驴的过程中,阿强和小灰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小灰很通人性,阿强一个眼神,它就能明白主人的意思,有一次,阿强在集市上忙得晕头转向,不小心把钱包落在了摊位上,等他发现的时候,已经走出了很远,小灰似乎察觉到了主人的焦急,突然加快了脚步,径直往回走,阿强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,等回到集市,看到钱包还在摊位上,才明白小灰是回来帮他找钱包的,阿强感动得抱住小灰的脖子,说:“小灰啊,你真是我的福星。”
随着时间的流逝,赶驴这种传统的劳作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但那些赶驴的日子,却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记忆中,无论是王大爷和黑宝,老李和大壮,还是阿强和小灰,他们之间的故事,都是乡村生活的珍贵宝藏,那些赶驴的岁月,充满了汗水与欢笑,见证了乡村的变迁,也承载了人们对过去生活的深深怀念,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中,这些赶驴的故事,就像一首悠扬的老歌,让人回味无穷,也让我们更加珍惜曾经那段简单而又美好的时光。